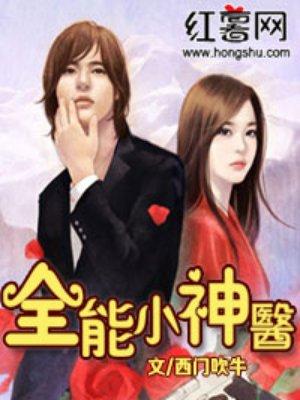爱我小说网>风前絮(权力的游戏) > 落月宠物医馆(第1页)
落月宠物医馆(第1页)
严忍冬嘴角终于笑了,单手还插在那人腹中,却撑着断臂站起来,把他持拎在空中。
血像加压的水车一般喷溅而出,他露出比雪还白的两排齿牙,在黑夜里无声地、忘情地笑着。
那人已经死去。
严忍冬依旧持着他,像是对他的魂灵说道:“我是一个杀手,一个被暗卫,被亲爹训练过的泥腿。”
他越说越咬牙,越说越仇恨,声音渐渐虚了,整个脸面扭曲着道:“你们怎么敢这样对我?”
他拍拍那死去狱卒的脸,声音逐渐大起来:“敢拍我的脸,踹我的肚子,断我的手,撕我的纸,侮辱我的意志!”
他如鬼魅罗刹般转头看向那门槛上活着的人,那人颤抖着道:“壮士。。。壮士饶命,壮士饶命,刚才。。。拍你的脸,踹你的肚子,断断断。。。断你的手,撕。。。你的纸的人都都都都是他他他他他。。。。。。”
严忍冬把那死人一甩,浑身是血地走过去。
那人已无路可退,只滚身在地上爬,边爬边道:“至至至至。。。于意志,我我我我我听听听听不懂。”
“很好,”他在他面前站定,又缓缓附身下去,那狱卒吓得双肘往眼前一档,叫道:“壮士饶命啊!!!!”
严忍冬一把掐住他的脖子,嘘声道:“想活命,就别叫。”
那他呆愣地点点头,仿佛已经没了意识。
“我给你一个机会,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,”他像是疯了,“你刚才不是说,命贱生下来做牛做马不值吗,不是想做生作死吗?”
“没没没没。。。没有,作作作作作生作作作死,现现在就在在在作作作生作死了,并并并不不不爽爽爽爽啊。。。啊!!!”
严忍冬又狠狠掐住他,“壮士饶命!!!我做做做,您叫我做什么,我做什么!”
他虽被拎着,却做出磕头的姿态:“只要您不杀我,只要您不杀我!”
严忍冬收回放纵的表情,把满手的血在他脸上揩着,就像今日白天,被那菜农陈刚把手上的泥蹭在自己身上一样。
那泥珠子现在还覆在袖口,严忍冬笑了笑,把狱卒往地上狠狠一推,站起来说道:“三件事。”
“第一,把这里处理好。第二,带一个人回去,让他犯错换岗,抵了这死人的差。第三,”
他从袖口掏出那张字条,食指中指夹着,居高临下地递到狱卒面前:“把这个交给你们大人,告诉他朝中有人谋逆,叫皇帝亲自来问我。”
那人颤颤巍巍地接过纸条,一眼都不敢看,颤声道:“是。”
这三件事一件他都没底,可以说件件他都做不成,但此刻为了生,不得不装作件件都能做。
不,是不能做也必须能做。
人活得那么苦,在真正的死面前却毫无退路。
严忍冬蹲下来,浑身的血腥气逼压过来:“从今以后,你就是我的人,若你敢卖我。。。。。。”
“不敢不敢不敢,”那人捧着纸拜伏,“从今天开始,我生是壮士的人,死是壮士的鬼,我守口如瓶,我我我。。。我尽心尽力,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!”
严忍冬鼻子里哼一声气,站直身道:“一个时辰,我去找人,你把这搞定了,带着你的狗滚。”
次日晨起,季府落月阁中一派生机。静堂带着梅若墨香,连并阁中一众丫头小厮在院中给流浪小狗洗澡。